The Mountains
8
道班的食堂竟然有干牛肉丝,泡在辣油里头,整个颜色鲜红透亮。趁此机会我买了整整一个饭桶,留着当零食。柯拿着我们两个得通行证跑到隔壁的办公室办手续,很快就回来了,让我去按手印,之后证就可以用了。我告诉他去前面的锅里舀汤喝。他喝得很少,大概是因为有牛肉,只是接满了桶里的热水。他食欲不怎么样,可能是因为墙上挂着的那个鹿头。
这两座平房是就地取材搭成的,松木,石块,然后黏土用来填上地面附近的缝隙,之后有两个旧的集装箱,夹在结构中间,用作道班的工具库。窗口边一条金毛狗跑到我脚边来蹭,然后抬起鼻子嗅我的手肘,尾巴摇一摇的。
“你看它喜欢你。”柯坐在桌子对面,犹豫不决地踮着脚尖,尴尬地挪到靠里面的角落。我把筷子放下伸手摸了摸它,然后它就把脑袋喂到了我手心里。
“这不废话么。”
“会不会咬人啊……”
“你连我都不怕,你怕它干什么。”
“它不会说话。”
“会说话的狗就不咬人了?”
他用力地踢了我一脚。
柯已经习惯了在路上的生活,他使用一种极其复杂但对他十分有效的方法来整理自己的碎片,从不会遗弃在路上。他在那个神奇的肚兜里藏了餐巾纸、笔、各种小本子、捡到的石头、硬币、钥匙、零食、该死的防狼喷雾。由于肚兜的左右是联通的,他常常在肚子前面抱着手上下甩,兜里的东西稀里哗啦地响。
村落前的空地上还停着两辆越野车,泥糊的纹理一层又一层地盖在车壳上,只有尾牌照最近被擦过,是北海那边的牌照。路边来了两只鸭子在等班车,有一个人深情地抱着路灯杆。
小车很快开到了丘陵的最高处,水箱前面干燥得没有一点霜冻,地平线四周明晃晃的,两面星月旗帜悬挂在一条钢丝上,有气无力地晃着。信号塔的影子硬梆梆地定在地上那个巨大的水泥箭头中间。柯从旁边的砖房出来,那里是枯岭的航空情报站,曾经作为东部山区的十三个通信中继之一,运输联盟的卫星导航搭建好之后,这些中继逐渐就不再使用,远程的航班早早地拐向了北海,这里的天上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。
他走在车顶,尝试将太阳能板掀开朝着太阳的方向,没法稳住,就又放了回去。冬天太阳能几乎发不出来什么电,因此需要每天多开些路程让电池充满。
“他们从黑匣子里查出来了什么东西没?”
“没有,新闻里没说,估计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“你不能从新闻里看。”
“那还能怎么样?昨天晚上我说要放电台,你说你要打瞌睡,还把天线头给我踢扯坏了。”
“新闻总是这样,什么东西都神神秘秘的,关键是大家还信了,你说这怎么回事,没脑子的东西。”
“没几个人关心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,得多留点时间关注比如贷款政策,以及红人们是怎么洗钱的,这些问题对市场冲击大,会影响我们的收入。”
“你觉得会不会是什么类型的干扰导致的?”
“那我倒想找到这帮人,问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飞行是自主控制的,要让它偏离方向不是像电影里那样随便发几个指令那么容易。我更相信是他自己的控制系统出了个什么问题,或者哪个临时工把插头插反了之类的。”
“难道就做不到么?”
“空中巴士前一阵子连着出了两次没有查出来原因的故障,都在南大洋附近,我看过下它们公开出来的报告,可能是附近的大功率地波站正在工作,使得迎角传感器的回报数字出了几个位的乱码。要我说可能是线束屏蔽不足,至少三个中两个出问题。”
“就像这个塔一样。”
“不,那完全不一样。它那有几公里见方的地盘,许多根天线排成阵列那样,人不能靠近,因为功率特别大。”
“我担心等不到我们有机会去,乘客线路就取消了。”
“咱至少还可以再活40年。”
沿途的地上一直躺着几条粗细不一的电缆,最粗的有两人合抱的样子。路边有时会有个铁架让他跨过路面,掉到另一侧继续前进。每隔十米的样子有一个橙色的油漆环,柯坐在“85502”上,两侧都是一人多高的枯草杆。我沿着电缆去追他,之后我们扑在草丛里打滚。
过了正午,我们进入了电厂的边界,再往前则是一片盐湖,抖动的白色轮廓逐渐从白热的地平线上滑下来。柯拿着盒子图摆弄着,头也不抬,一边拧旋钮一边在纸上勾画着地图上的纹样。车上小声地播放着一张很旧的碟片,是德州乐队的《天堂母亲》,唱机很快卡在了《我心中》的后半截,唱针走不动了。我捡起一张名片用力推了下盖子,唱针跳回到了《和你在一起》的末尾,之后又卡在了《我心中》。我把那碟片退了出来,随手在门把手底下摸出另一张放进去,是《生活的策略》。
下午的某个时刻,柯爬上了其中一个风车的某条钢缆,接近地面的位置几乎是平着的。他几乎可以躺在上头,只是轻微地随着上下晃动。由于直径巨大,风车的桨叶转得很慢,大概半分钟会有一片接近地面,倏忽间滑走了,轻微的漩涡声从一边飞到另一边。我坐在水泥路上,太阳硬冷地照着,产生了一种怪异的翕动,有点像淋着冷雨的味道,也可能只是进入了高原。
柯曾经说过,我应该到离月亮更近的地方去,他有一定几率是对的,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把衣服脱在车里,仅仅是毛就足够保暖了。
“说说看你有多久不让我摸你肚子了?”
“我只是忙着工作。”
“为什么你就不能在人的形态下也用这个声调?”
“因为人的声带非常薄,我不能只变一部分。”
“瘦了。”
“所以要多吃肉,现在我们去跑几圈。”
“你得让我抓着你睡一觉。”
“我现在浑身肌肉僵得要命。”
“我无限接近于想往远处丢一个网球,让你捡回来。”
“这么多年了你竟然手里连个球都没有。”
我在风电厂里绕了几个八字,大口喘气,出乎意料的放松。
他花了十天时间终于捣鼓清楚了那个白痴的慢炖锅是怎么回事:如果开关放在“高”,那么出来的功率是“低”,如果放在“低”,那么就是“关”,如果是“关”,则它有72.6%的可能性并不在关,而是处于“高”和“低”的量子纠缠状态。
太阳落山前,我们将车停在一座风车的锚点前面,望着窗外单调的晚霞,从远山的轮廓泄漏出去。他窝在我胸前画着一条狗,后腿换成了他自己的道具,结构有些问题,不过那暂时还没什么关系。他的小脚窝在毛里,我摸着他的耳朵,温温热的,那应该不怎么冷。我将盒子图调到我们大概的位置,离红水河还有三百多公里。我不清楚他今天想不想到镇上去住,但他应该不介意今晚就睡在我身上,既然是御用毛毯。
真想出去吼两嗓子。
第二天早上突然醒了,一夜未梦,叶片末梢的红灯几乎静止着,我突然有些饿了。柯还没有醒,车里的暖炉泵慢悠悠地响。我带着我的Kriss,轻松地走到锚地以外,装着消音器,鼻子还没有特别适应空气的温度。天破晓时,打到了两只野兔,大概八九斤重,我认为运气不错,一点薄雾帮上了大忙。
当一阵猛烈的刺痛撕开我的后背时,我正在用麻绳捆第二只的耳朵。被扑倒在地之前,一个影子窜上了灰黑的天上。当它回到我视野里,我看见是一只金雕。他的爪子竟然比我的脸还大,看那样子差点连我的头盖骨都能给插进去。它绕在我附近,我不敢大动,即使我并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好怕的。
“啊努——!”
我支起身子,回头看过去,柯站在后面,金雕落在他手臂上,翅膀半舒展着,柯伸出右手去钩了钩它的爪子。太阳从东南地平线升了起来。
“看样子你们两个不小心盯上了同一份早餐。”
“啊,见鬼,你们两个认识?”
“不全是,不过你好像让啊努很生气。”
“它几乎把我脑袋扯下来。”我从地上站起来,
“他只是厌恶你们这些用枪的。”
“所以我就得去死。”
“早跟你说过别在这里打猎,容易被针对。”
“被 针 对——?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,我今天心情不错,不然连它一块儿吃了去。”
金雕朝我吼了一声,难听死了,完全不是《动物世界》里的感觉,电视上什么都是假的。柯的鼻梁靠着金雕的喙,说了点什么,然后它飞走了,而且还不忘拿翅膀扇我一耳光。
“说说看你们什么关系。”
“我只是熟悉鸟的名字而已。”
“你不觉得这个描述本身就非常离谱么?”
“以后再跟你解释,或许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。背上有事没有?”
我盯着他。
他咧一个加宽的笑,丢过来一只兔子:“它给你留了只小的。”
“开车去。”
他朝我们的小车走了回去,手揣在外套里,一边走一边用脚去踢地上的石头,兜里的东西稀里哗啦响,延长的影子在地面投射得像电影。我逐渐反应过来,他与世界的联系可能远比城市丛林广得多,然而我不知道那能用来干点什么,也无法理解其中可能隐藏的别的东西。我了解一个二元角色论,故事的主人公要么会英雄地死去,要么成为黑暗的左手。我得确保柯成为黑暗的左手,不然的话,他已经给我规定好了——我是那个坏蛋。
有事。非常有事。他妈的,今天晚上别想再趴我身上。 | 

 Web Gallery
Web Gallery Comic: Blowback
Comic: Blowback Blowback Extras
Blowback Extras  The Continent
The Continent Cloud Travel
Cloud Travel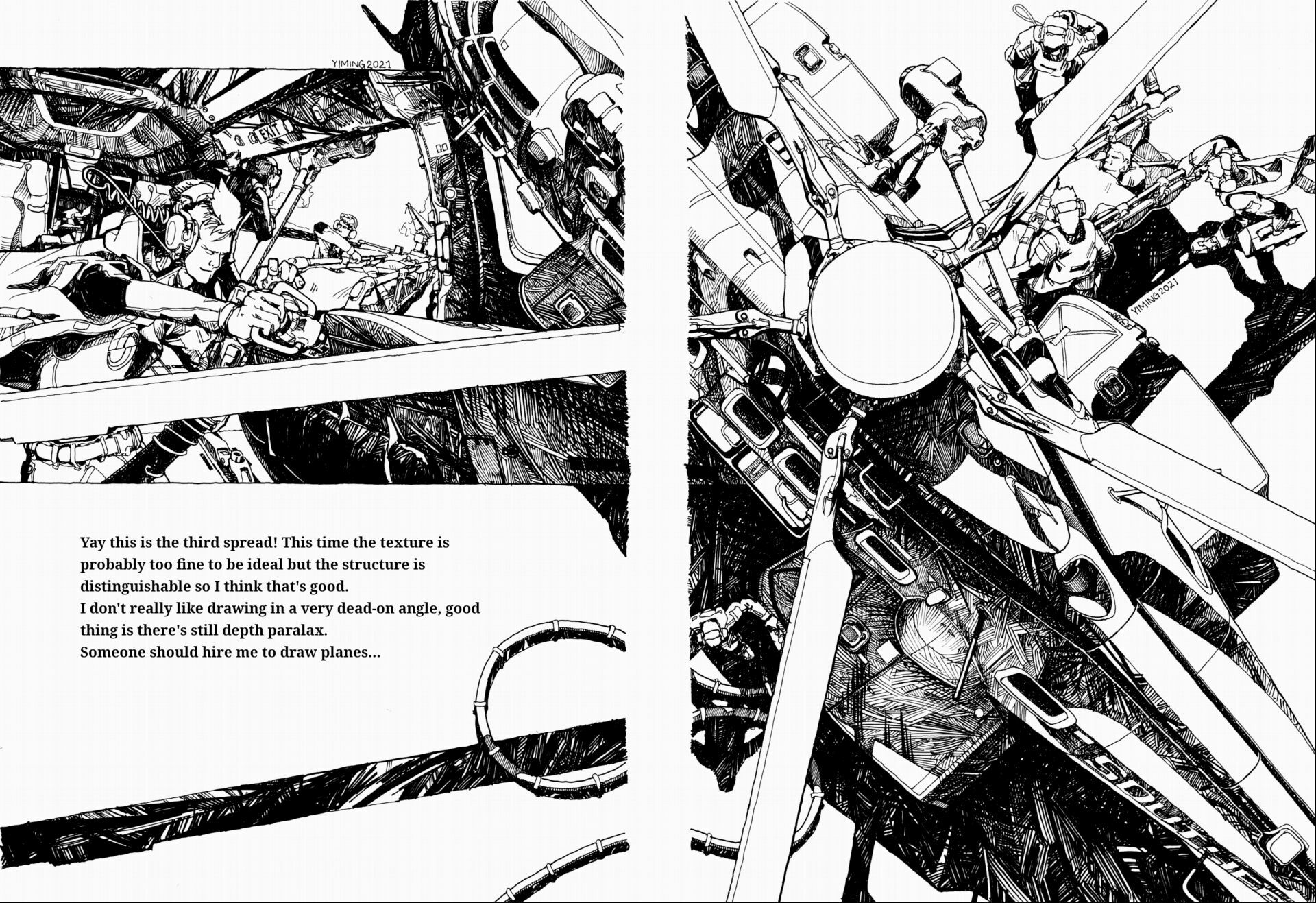 Comic: Rescuer
Comic: Rescuer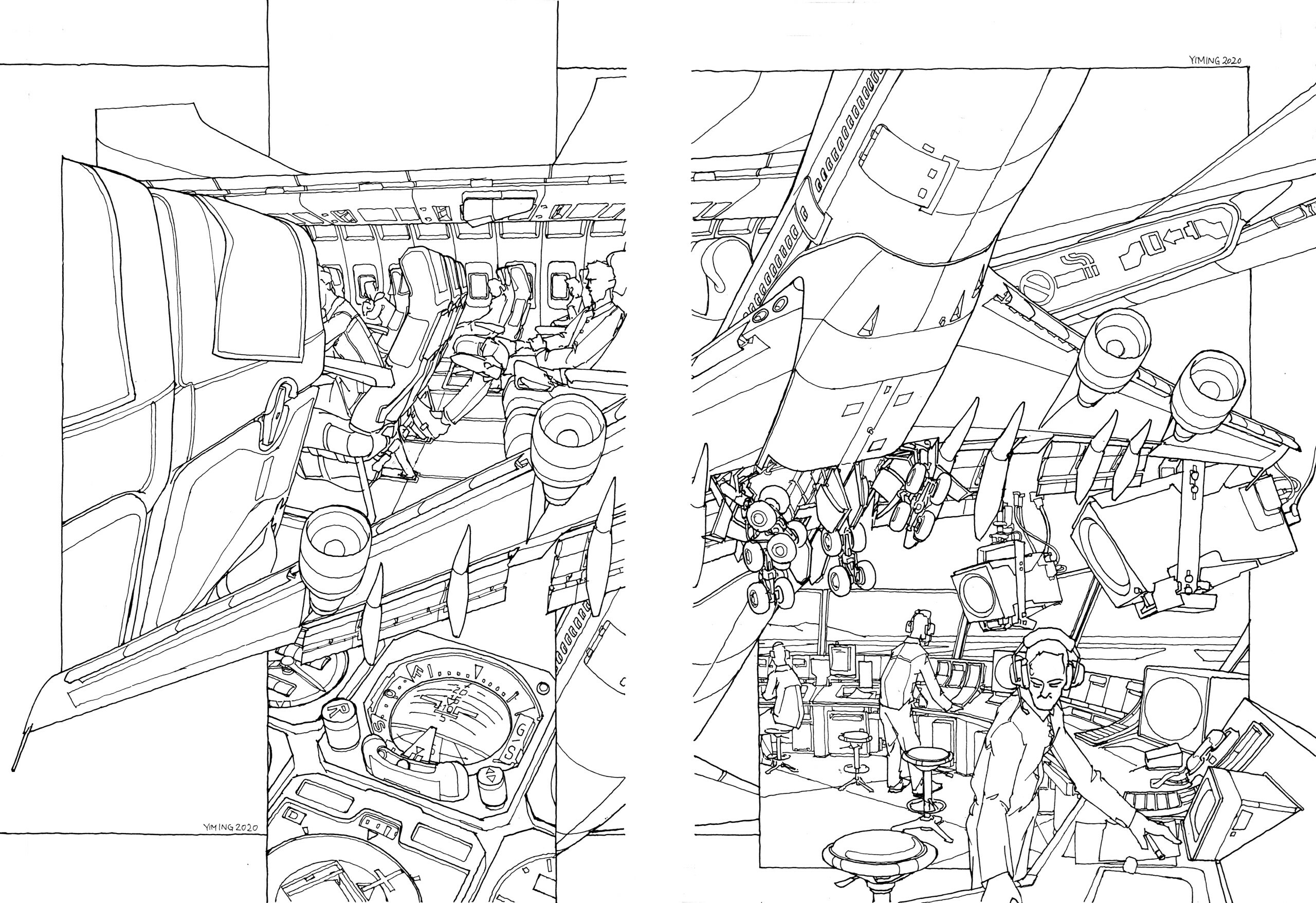 Comic: Flight 811
Comic: Flight 811 Comic: Slide
Comic: Slide Font Plug-in Manual
Font Plug-in Manual







